2002年8月17日是我的公公陈乐素教授百岁冥诞,他是现代宋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不但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宋史论著,还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宋史专家,如宋晞、徐规、程光裕、陈光崇等;他的第二、第三代弟子更是遍布海内外。200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在广东珠海市联合举办纪念他百岁诞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他的儿媳,希望以我浅薄的认识,从我亲见亲闻的角度,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和为人处世的风范。
一、第一印象
20世纪50年代末,我带着简单的行李,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智超已经是第二次来接车了,因为旅途疲惫,我在武汉休息了一天,耽搁了一天的行程。我们雇了三轮车到达陈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乐素先生和夫人洪美英女士为了等我的到来,还没有休息(后来才知道,他们一般晚上十时就寝)。我走进陈家门,第一眼就发现,他们的形象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一点都没有架子,对我这个远方来的小客人亲切慈祥。美英女士性格外向,端详着我,问我一路上的情况。乐素先生比较内敛,只是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说长途旅行已经累了,要我早点休息。看他们待人那么真诚、随和,我也就没那么拘谨了。
当我定下心来,环视室内的布置时,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这里不是花园洋房,而是带套间的两间旧平房,坐北朝南。外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三面墙排满了书架,书一直堆到屋顶,大部分是线装书。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盒装的二十四史。一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十八寸的大照片,是乐素先生与朱文叔向毛泽东敬酒的场面。室中还有一排书架,兼作屏风之用,两边分别是两老的书桌,乐素先生的书桌上堆满书刊。一进门有张餐桌,配了几张方凳,还有一对旧沙发和一个碗柜。里间是卧室,大约十四平方米,摆着一张旧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放台灯的小桌子,一个有自来水管的洗脸池。厕所在院子里,距住房五米开外,是公用的。没有厨房,一个蜂窝煤炉摆在门外的屋檐下,到冬天就将炉子搬进屋里,安上烟筒,兼作取暖之用。另外还有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在同一排,但隔了几户人家,是两个上大学的儿子周末回家时住的地方,现在成了我的卧室,他们回来,我在大屋搭个铺。这样简陋的陈设(以后又看到周围几家都大同小异),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情况。一位受人尊重的历史专家,物质生活如此简朴,却兢兢业业地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他有着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1956年2月3日,在全国政协晚宴上。中为朱文叔。
第二天,美英女士带我到全院走了一圈,我才知道这里原是乾隆皇帝的一座公主府。一进大门是一个很大的荷花池,院内还保留有当年的戏楼,现在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两座较新的楼是办公楼,其余的则是职工宿舍,我们住在大院的最北面,一排平房,住着十余户人家,都是乐素先生的同事。慈祥而稍带严肃的乐素先生,除了书籍之外,只有简朴家具的陋室,这就是当年我的第一印象。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经过高中补习,考上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搬到了学校。后与智超结婚,成了陈家媳妇,与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他们的了解与敬爱与日俱增。
二、父亲的熏陶教育
陈垣先生二十二岁时得子,为他取名博,乐素之名是后来改的。当时陈垣先生在广州与友人潘达微、高剑父等合办《时事画报》,负责报中文字工作,用“谦益”等含有反满意味(满招损,谦受益)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反对列强侵略的文章。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他经常转移住处,因此将儿子留在家乡由妻子扶养,直到乐素先生五岁时才把他接到广州。
乐素先生虽然只在家乡生活了五年,但对家乡始终怀着眷恋之情。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回乡,指着故居右上角的一间厢房,动情地对同行的亲友说:“我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他还把从新会带回的茅笔(陈白沙曾用茅草札笔写字)送给我和智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见他用浓重的乡音吟诵陈白沙的诗句:“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蚬壳,巷口挖泥沙。而今年长大,心事乱如麻。”他闭着双目,拖着长长的音调,儿歌式的诗句,把他带回到多年前的童年。他说,这是四五岁时在家乡学会的,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儿时诵读的诗歌,至今没有忘记。
1907年乐素先生五岁,陈垣先生把他接到广州,住在“陈信义”药材行中,和店员同桌吃饭,学习到了一些有关药材的知识。他先在“陈宁远堂”的家塾中学习过一段时间,然后进了教会办的圣心书院和岭南小学。他曾几次谈到在广州这段时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他七岁的时候,陈垣先生给了他一套《三国演义》,并让他把每一回中首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把他们记熟。这样阅读《三国演义》,既锻炼了记忆力,又接受了中国文史的启蒙教育。另一件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不久。有一天,他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仲益,趁父亲不在打开他的抽屉,竟发现藏有一把手枪。他们当时只觉得好玩,抢着来玩。不料手枪走火,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砰然作响,好险啊!此事如果走漏出去,还将有杀身之祸。后来还是由一位族叔买了一张船票,在开船前将手枪从厕所中扔进珠江,全家人才算松了一口气。两兄弟也模糊地感觉到了父亲的革命党人身份。
陈垣先生在民国二年(1913)当选为众议员,从此到北京定居。乐素先生十四岁(1916)小学毕业,陈垣先生把他接到北京上汇文中学;1918年,又把他和仲益送到日本留学,当时他十六岁。
乐素先生在日本就读的是东京的明治大学,专业是经济学。陈垣先生不断通过书信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又让他利用留学的机会,多去聆听学者的学术报告,并到图书馆帮助他搜集有关历史的资料。现在还保留着一册乐素先生当年为陈垣先生抄写的一部宗教史资料。封面是陈垣先生题的书名“两眼考”,还有他的批语:“一九一八年六月博儿钞于东京帝国图书馆”。乐素先生在陈垣先生的熏陶、教育下,逐渐对历史与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在记忆力和读书方法上得到锻炼,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众多弟妹中唯一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的人。
三、从投笔从戎到以笔作枪
在日本留学四年后,乐素先生回国,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培英等中学讲授历史和语文,这是他正式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另外,在课余时间他系统阅读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为日后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乐素先生从小就敬仰孙中山先生。1926年北伐前夕,广州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青年的乐素先生受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毅然放弃教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第五军任政治宣传员,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理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但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国民党左派人士也遭到迫害。乐素先生在徬徨苦闷中到达上海,先在民众烟草公司暂时栖身,不久正式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
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1929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杂志的主编,先后发表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等论文。他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在日本留学时,一方面,对日本学术界重视中国文化,深入细致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刻苦钻研的精神,深为佩服;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有些日本学者的研究目的大有问题,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为日本侵略中国以至亚洲制造舆论。在史学领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他要透过自己的研究,恢复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真面目。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使他将研究方向转至宋史。由于当时的当权者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而且还步步进逼,华北岌岌可危。中国面临亡国威胁。作为一名爱国的历史学者,乐素先生深感有责任从历史上寻找救亡图存的借鉴。过去他通读中国历史时就已注意到,宋代是一个“外患”频繁的朝代,有许多情况与当时的现实相似。于是他发愤钻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文章指出,后晋石敬瑭甘当“儿皇帝”,将幽、云等十六州割让与契丹,自尝恶果,至出帝被掳而亡国。宋徽宗谋复燕云之举,在于恢复原有之疆土,“此种思想绝不能谓为谬误”。至于谋复燕云之失败,则在于“当时之君臣实暗弱庸陋”,“事先无缜密之计划与充分之准备”,非战之罪。文章还批判了当时的反对派以为在辽金之战中采取中立态度即可保无事的观点,反问道:“然则金既灭辽,宋能否遏止其南侵之野心?”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对他谋复燕云之举,乐素先生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反观作此文时的现实,文章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在此以后,他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徐梦莘考》和《三朝北盟会编考》两篇长文。这些论著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宋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四、艰难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月,又发生“八·一三事变”,日寇进攻上海。乐素先生带领全家六口匆匆离开上海到香港,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一次大逃难,当时二儿子刚刚满月。到达香港后,经许地山先生介绍,乐素先生在英华女子中学得到了一个教职,讲授历史和国文。为了维持一家七口(1939年小儿子出世)的生活,每周授课时间至少二十几小时,有时甚至更多。即使在这样繁忙的教学生活中,他仍保持充沛的精力,乐观的态度。他爱好运动,特别是游泳,能从九龙游到香港。他还抓紧教学之余的时间,开始了《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的写作。智超曾回忆,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父亲还让他们姐弟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人分几卷,将其中提到“宋志”或“宋史艺文志”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标完之后,交换复查,凡有查出遗漏的,发一件小礼品。有时父亲还带着他到图书馆帮着抄资料。当时他年龄小,不能理解资料的内容,所以就只当作写字练习。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在东南亚全线出击。原驻守在九龙的英军全部撤到香港岛,从广州南下的日军一时还没有到达,九龙出现了几天政治、军事上的真空时期。地痞流氓把这当作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他们大呼“胜利啦!胜利啦!”划分地盘,挨户抢劫,九龙陷入恐怖之中。
乐素先生全家住在九龙通菜街二三八号三楼,这时他的两位姑姑以及弟弟一家三口都来避难。劫匪把住楼门口,从一楼抢起。乐素先生听到劫匪从二楼上来,主动把门打开。后来谈起这件事,他说这叫“开门揖盗”。因为你不打开门,他们会把门砸开,财物照抢;主动开门,还可以把门保住。劫匪进门,看见满屋都是书,不禁皱起眉头,大声喊道:“你们把钱藏在书里,叫我们怎么找呀!”书、输同音,他们认为不吉利。乐素先生事先已有准备,主要的钱财确实夹在书中,但也在抽屉等明处放了些财物。他听到劫匪们的谈话,突然说了一句:“乡里,我们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呢。”小头目问道:“你是哪里人?”答道:“新会石头。”小头目不出声了,匆匆搜索了一下就转到对门一家葡萄牙人家中继续抢劫了。全家人正稍稍定下心来,忽然又听到拍门声,不知又会出什么事。开门一看,劫匪下楼了,留下一小袋米。“米来了”,广东话谐音“不来了”。劫匪以后真的没有再来过,而附近有的人家被反复抢劫多次,甚至连牙刷也不放过。乐素先生的从容镇定,保住全家免遭更大的损失,也令亲友钦佩不已。
日军占领香港后,学校停课,生活来源断绝。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乐素先生只好到半山私人别墅里教授日语。日军经常突然实施戒严,滥杀无辜,他每次去讲课,都要冒风险。即使是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他也尽力帮助别人。那次劫匪走得匆忙,一大袋放在楼梯脚下的白米居然免遭劫掠,这在当时真是全家的救命粮啊!但当袁同礼先生来访,久久没有去意,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家中缺粮,出来找米,又难以启齿,乐素先生慨然以米相赠。当他知道陈寅恪先生家中断炊,又带了一袋米送去。为了顺利通过日军的关卡,他还把当时年仅七岁的智超带在身边以作掩护。陈寅恪此后十分念及这段旧情,曾在乐素先生临离香港前把自己在英国演讲时所穿的一套西装赠送给他,留作纪念。
1942年底,乐素先生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到当时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大史地系任教。他带领全家七口,离开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开始了第二次大逃难。他们经澳门、广州湾,跨过寸金桥,进入大后方,然后辗转到达遵义。他在浙大史地系开设了唐宋史、日本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尽管当时物质匮乏,资料又缺,但他精心讲授,循循善诱,深得学生的爱戴。
1945年上半年,是内地公教人员最艰难的时候。大学教授的工资只能买米七斗。乐素先生五个子女,四个辍学,孩子们每天帮助美英女士在街边摆摊出卖家中仅存的旧衣物。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家中生活偶有改善,他也必定把那些家在沦陷区、生活来源断绝的学生找来共享。多年以后,这些学生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怀念老师、师母当年请他们吃的“营养菜”。其实这不过是卷心菜、西红柿、胡萝卜再加少量五花肉而已,但在当时已是难得的佳 ,并饱含了他对学生的一片真情。
,并饱含了他对学生的一片真情。
五、“文革”厄运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浙江大学全校复员回杭州。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之江大学合并,改名浙江师范学院,史地系撤销,乐素先生任图书馆馆长。1954年,他从杭州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同时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56年,他主持并和巩绍英、邱汉生、汪篯、王永兴等专家共同精心编写的高中中国历史课本正式出版,受到史学界、教育界和全国历史教师与学生的高度评价,同年2月他还作为教育部三位代表之一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正当他准备和同事们进一步修改、完善全国统一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并撰写历史研究所重点项目“中国史稿”的宋代部分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革”对全中国人民都是一场灾难,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一部分。乐素先生在“文革”中经受过多次冲击。
“文革”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乐素先生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是“反动权威”陈垣的“孝子贤孙”。当时造反派还追问一件事,这样的“反动权威”怎么会钻到“林副主席”身边?原来,1962年左右,历史所按中央军委的要求,选了几位研究人员为林彪的妻子叶群讲历史课,乐素先生也去讲了几次。这件事当时严格保密,智超和我都不知道。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它又变成了“投靠”林彪的“罪行”。

乐素、仲益、约、容四兄弟在兴化寺街5号院,时为1950年。

1954年调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夫人及女莲波、子智仁、智纯合照于北京。

1957年5月摄于北京香山香炉峰。

1962年回广州,与弟合照。

1959年摄于兴化寺街5号院内。陈垣先生抱者为曾孙超英。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乐素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美英女士焦急万分。后来才知道被出版社的造反派“隔离审查”了,就关在大院的洗澡房内。紧接着就是两次抄家和封存办公室,许多珍贵书籍至今没有下落。这一关就是四个月,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原来乐素先生在浙大的一位老同事,在杭州大学,“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屈打成招,把浙大教授会的成员都供作特务。
因为查无实据,造反派只好把他放出来,但马上又被打发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近古稀,但白天要挑几十担水供全连(干校按军事编制)使用,还要送报送信、夜里则经常要到稻田值班看水。有一次挖开田埂放水,因为天黑,铁锹伤脚,血流如注,伤口见骨,他忍痛坚持到天亮接班人的到来。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乐素先生接到勒令退休的通知。他想回北京,但当时领导干校的军宣队宣布,只能安置到县以下的地方。最后考虑到他年纪已大,才“开恩”让他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多年的杭州。
虽历经种种磨难,他身体不垮,精神不倒,因为他自信一生无愧,把这些磨难当作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回杭州后,几乎天天步行十几里到浙江图书馆看书,继续进行《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写作。
六、老当益壮
19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知识分子得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工作。1978年,浙江省为一批老知识分子重新安排工作,乐素先生是名单中的第一位,担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并被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次年又照顾他叶落归根的愿望,把他调到新复校的暨南大学,以后又请他负责筹办古籍研究所。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1984年他到香港参加宋史国际研讨会,与阔别多年的浙大老学生宋晞重逢,还会见了海外一些久慕其名的中青年宋史研究同行。

1976年自杭州来北京看书,摄于智超家中。

1976年与智超合照。

1976年与智超、庆瑛合照。

1978年与智超合照于毛主席纪念堂前。

1978年与智超、庆瑛合照。
“文革”以后乐素先生进入了他一生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发表了《宋代客户与士大夫》、《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等十几篇论文,结集出版了《求是集》一、二集两本论文集,并对《宋史艺文志考证》作最后定稿工作。
1979年他调到暨南大学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他不只一次满怀信心地对人说:“今人八十不算老,我至少还要再干十五年。”我原来对此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乐素先生与同年龄时期的陈垣先生相比,健康状况要好得多,而陈垣先生即使经历“文革”的磨难,也享年九十一岁。但万万没有想到,乐素先生竟在1990年7月20日还差一个月八十八足岁时,因肺部感染而病逝了。事后细想,乐素先生如果能适当考虑自己年事已高的现实,量力而为,寿命超过他父亲是没有问题的。
乐素先生一生喜好运动,青年时还练过健美运动,很少生病。直到晚年,还坚持每天至少步行万步。登山爬楼,许多中青年都赶不上。有的人是“不知老之将至”,他则是“不知老之已至”。逝世后检查他的遗物,没有发现任何遗言,他根本没有考虑有朝一日的身后事。这反映了他的洒脱,也反映了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高度自信。
七、我的遗憾
无论是在我和智超结婚之前,还是以后成为他的儿媳,乐素先生都把我当做他的子女。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他和美英女士亲自送我到民族学院报到,而他们自己的两个儿子入学,都是自己扛着行李去学校报到的。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他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线装《资治通鉴》送给我,勉励我好好读书、工作。
回顾我和公公相识、相处的三十多年,有三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到北京后不久,乐素先生和美英女士真诚、亲切,很快就消除了我当初的惧怕和拘谨。但当时我年纪还比较小,在一个与我过去经历完全不同的环境住下来之后,又感到难以适应。即使像吃饭这样的生活常事,我是云南人,喜欢吃辣,口味也比较重;他们是广东人,口味清淡。吃饭时,两老自然是用他们习惯的广东话交谈,刚开始时我简直像听天书(后来我正是透过这种餐桌谈话听懂了广东话)。诸如此类的事使我想家乡,想同学,心情不好。以致有一天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蒙头大睡,不吃不喝。美英女士急性子,见我不出来吃饭,给我送饭,我不理。第二天,她急得不行,把乐素先生搬来,我还是不理。他说:“小瑛,不吃饭可不行。我把饭放在窗台上,你自己拿去吃。”我还是不理,饭在窗台上搁了两天。邻居孙士诒先生也是位老编辑,他看不过去了,跑来敲我的门说:“你知道你在跟谁发脾气吗?乐素先生是我们全社都尊重的老专家,谁都不敢、也不会去顶撞他。你这黄毛丫头,他给你送饭都不吃!你再不出来,我就把门砸开!”听了他的话,我终于觉悟到自己太任性了,于是开门吃饭。乐素先生见我走出来,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只是说:“你还年轻,要好好爱护自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也深深自责。
第二件事是我与他发生的唯一一次冲突。那是在“文革”爆发以后,原来安详宁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一时变得杀气腾腾。造反派在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四处串联,小孩子则跟在大人后面瞎闹,以后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当做整人的工具。“牛鬼蛇神”的孩子说了一句当时的“错话”,造反派就借此对他们的家长大肆讨伐。
我的孩子还小,在家待不住,总喜欢跑到大院去玩,时常被大孩子打骂。乐素先生心疼孙子,也怕他“闯祸”,要我每天把他带去上班。我们学校也无例外地在闹“革命”,不让带孩子上班,我只好把他放在学校附近的月坛公园,让他在那里看小人书,下班时再把他带回家。头三天总算平安无事。第四天下班后我到公园去接他,四处不见人。一个士兵看见我焦急的样子,问我是不是找孩子,我说是。他带我到一个拐角处,指着缩成一团的儿子说:“是他吧!你怎么不好好管教他?他钻进电视转播塔里,这是机密重地,要不是看他年纪小,早就把他抓走了!”他要我把单位、姓名、地址等登记下来,才让我把儿子带走。回家路上,我看孩子满面泪痕,问他是不是挨打了,他点点头。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无可奈何,我只有把他留在家里。第二天我去上班,乐素先生见我没有把孩子带走的意思,提醒我把他带走。我说以后就让他留在家里。他说:“不行!你没有看见大院乱成什么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边哭边诉说昨天的事,并说:“有家不让待,还算什么家?要把他放在大街上,你去放好了!”他没有再说话,我一甩门就走了。不久他就被造反派抓走,孙子的事想管也管不了。事后回想,我虽然无可奈何,但对他当时的处境和苦衷也理解不够,总有负疚之感。乐素先生历经风浪,每次在危急关头总是镇定从容。但“文化大革命”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常规,使他无所适从。他处境已经险恶,还要尽力保护老父、爱妻、子孙,至少也要使他们免遭新的打击及迫害,于是处处小心,处处提防。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些努力总是徒劳。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知识界的悲剧。
第三件事是我未能见他最后一面。智超是1990年7月18日得到他病重的消息的,连夜从北京赶飞广州,到家已是19日凌晨。19日白天智超都在病床边,乐素先生谈话虽然吃力,但精神还不错,没有想到20日上午便离开人世了,当时我在巴黎进修,智超在电话中告诉我这悲痛的消息,我半晌无言,只能在万里之外默默地祝他走好。
2000年11月,我和智超到江门市参加纪念祖父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以及陈垣故居被批准为新会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揭幕式。我们约定,归程一定要在广州停留一天,以了却我十年来的一桩心愿。我们去了银河公墓,在公公灵前献上了一束迟来的鲜花,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
这么多年又过去了,这篇短文,就是我献给他的一炷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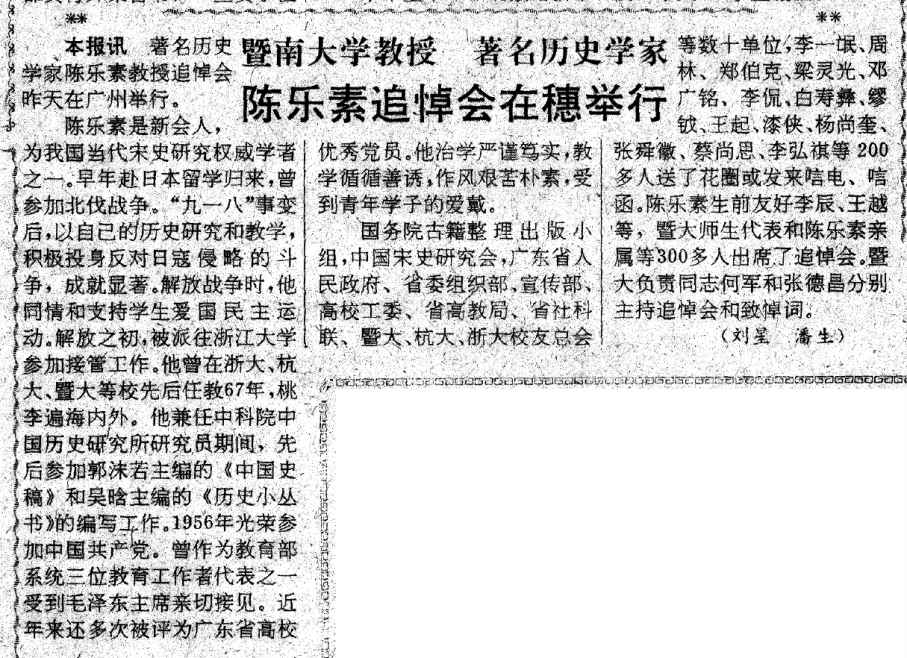
1990年《羊城晚报》报道追悼会消息。
